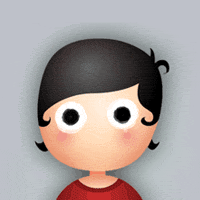我辣故我在
酸甜苦辣咸,食之五味,唯辣为异。为毛?因为酸、甜、苦、咸乃是味觉,感受的触端来自味蕾。而辣,却是一种痛觉。科学家叔叔告诉我们,痛觉会引起大脑中内啡肽的分泌,从而平衡痛感,使人感受到某种妙不可言的快感。不吃辣的小朋友不妨去采访一下身边那些喜欢剥去伤口血痂,或者爱撕手上倒切皮的同学,大概能了解个一二,触类旁通嘛。恩,喜欢吃辣大概就是一种安全的,低成本的,无伤大雅的,人畜无害的,小小的自虐行为。痛觉总是更深刻一些。
有人把CHINA翻译成“吃辣”,大约是蕴含着全民皆辣的美好愿景。但中国人嗜辣与否,这永远是一个无法统计的宏大数字,就我来看,近三十年,确实更多的人爱上了这种痛觉。痛,并快乐着。
第一次被辣这个痛觉俘获,是在大约6、7岁的时候,在“花子”家。花子是我爸妈的同事,来自蜀地,我已不记得是成都、重庆还是乐山,但以80年代来定义,称之为四川人在地域上或行政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我儿时所在的小地方,汇聚了如“花子”家一样从全国各地来到此处建设新中国的叔叔阿姨们,温暖甜腻的80年代人间氛围,让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在人与人之间流转,也早早打开了我对味觉痴迷的开关。
现在想来,对花子家的回忆简直是太美好了。我热爱那段时光,以至于我到现在还能回忆起他家的那幢楼,楼梯上石头扶手充满包浆挂瓷的温润手感,乃至楼道里那堆杂物。只要回想起,我仿佛一伸手就能够到他家里屋门背后挂着的拂尘,那应该是我与有着武侠意味的符号第一次亲密接触。
花子有两个儿子,与我交好的是二子。二子哥哥比我大着几岁,能临摹一手好贴纸,能按着贴纸上的样子,将那些变形金刚和百兽王画得惟妙惟肖。我曾央求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上一个博派的标志,在那个时候的我看来,简直神乎其技。我开始嗜辣也与二子有关。
那是一个我已忘却季节的某一天晚上,花子阖府统请,邀我全家共进晚餐。这在我记忆中也是相当平常的事,好像三不五时就会去赵叔叔、钱阿姨、孙伯伯、李妈妈家吃一顿,当然我家也会时常有些叔叔阿姨来吃饭。也不是吃席,家常便饭而已,谁家做了肉了,谁家钓到个王八,要么碗盘相送,要么索性共箸齐勺。人情味那是一定的,不似如今,给邻居送去个八宝饭,邻居还回一水缸狐疑的神色,恨不得银针伺候。
那天晚上吃饺子,对当时的我来说,饺子已不陌生。每月总有那么一次,老妈会包饺子。通常是韭菜肉或者芹菜肉的,绝少有纯肉的。偶尔也会来个黑暗料理,萝卜馅之类的,让我恨得直哭。所以我对花子家的饺子没有太多的期待,饺子嘛,擀个皮子,放上剁烂的馅,两边对折捏一捏,滚水下得了沾醋吃,没什么稀奇的。但二子当天的吃法,足以让他成为我在嗜辣之路上的导师。
一盘饺子端上来,我已开吃,夹起一个,醋汁里打个滚便往嘴里送,嗯,仿佛是比咱妈做的好吃些,符合“菜是别人锅里的香”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二子不慌不忙,拿过一个大蓝边碗——不稀奇!80年代全国人民十有八九手中端的都是这种碗——然后取来一个瓷罐,罐中是洁白似雪,丰腴诱人的猪油,㧟了一勺放在碗里。唉,猪油!那又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恩物,让我真切理解了什么叫猪浑身都是宝。
看到蓝边碗里的猪油,我已疑惑,已不记得要将勺子里的饺子往嘴巴里送。这是要做什么?醋里点香油已经是至上的美味了,二子哥哥是要醋里拌猪油吗?我不太记得那个当下,二子这厮有没有对我诡异地一笑,但我确实已经被他正在做的事情吸引住了。二子如同一个巫师,先是猪油,再兑上酱油,然后才是醋,最后才从一个原先用作水果罐头的玻璃罐里舀出两勺红彤彤的膏状物质放到碗里,在二子筷子的搅拌下,碗里的黑白红变成了和谐的绛色,油亮可人。更有屡屡异香袭来,那种另类的,不曾尝试过的香味,直接影响了我的大脑,再看我面前的醋汁,已寡淡如死水一般。二子捧着蓝边碗走进厨房,再出来时,碗上氤氲叆叇。这只满含饺子的蓝边碗就在我的眼前,二子拿起筷子翻动着饺子,顿时,原本白白胖胖的饺子胭脂绯绯,直如年画里抱着鱼儿的童男童女,还有比这更可爱的画面吗?那一刻于我,灵感大王附体,童男童女,我所欲也!
我弱弱地问二子:“二子哥哥,给我吃一个吧。”二子骄傲(嗯,一定是骄傲的)地回我:“不行,你吃不了!”WHAT!竟然说我吃不了!我猜想,我当时脑海中一定划过了、、,至少是赖宁的名字。?抢!我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仁不让之势从那只闪烁圣洁光芒的蓝边碗里抢过一只“童男”塞到嘴里,然后……
我哭了,嚎啕大哭。鼻涕眼泪俱下,太特么辣了!舌头立时成了蛇信子,口腔灼烧起来,嘴唇以极高的频率颤抖。这几样东西似乎要挣扎着从我身体上剥离出去。我耳朵还算灵敏,我听到了哄堂大笑,二子爸、二子妈、我爸、我妈、还有二子老师,唯独我,独怆然而涕下。
这是我第一次自虐的经历,正如法律明文禁止的那些丸散膏丹一样,我初尝此味便已万万劫不复。那次之后我迷上两种滋味,一种是辣,一种是麻。前者来自辣椒,后者来自花椒,嗯,正是我嘴唇高速运动的动力来源。二子的吃法应是脱胎于红油抄手,好多年后我第一次在成都吃红油抄手时方才恍然。这件事在之后的许多年都成为我妈爸口中的笑谈,我也开始了嗜辣的生涯,这种感觉极其良好又不足为外人道。以后我在许多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作品中找到类似的感受,大姑娘洞房一夜,次日醒来对着落红嘤嘤自泣……还是不方便细说,总之,痛,而后快乐着。
嗜辣伴随着我长大,用到“嗜”字,自然要比“爱好”更重口一些,在相当一段日子里,我吃什么都放辣,饺子面条白米饭,馄饨馒头和大饼,但凡能放些辣的,那绝对不做第二种调料选。因为我口味的变更,家里的口味也随之而变,偶尔寒暑假来我这里二弟——一个地道的上海小孩——也爱上了辣。以至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兰州拉面店斗吃辣,你一勺我一勺将一整罐油泼辣子都放进碗里。
刚回到上海时,爱吃辣成为我的标签之一,我亦欣欣然,但凡有人说一句:“哟,格小胖友蛮能吃辣额嘛!”我便会人来疯似再多放几勺辣酱,以佐我的洋洋自得。常光顾的卖“包脚布”的小摊老板娘也被我调教得远远看到我,就心灵神会地念叨:“弟弟,两只蛋,重辣。”夜半三更去长脚汤面,不待“长脚”问要微辣、小辣、中辣、大辣,我便高声一喝:“O辣(沪语,恶辣)!”,在众食客或歆羡或诧异的眼光里沾沾自喜。法显在《佛国记》中说“击木以自异”,当时的我大概是有些“嗜辣以自异”的。渐渐地,上海也开始流行起来川菜,水煮鱼、沸腾鱼、酸菜鱼、麻辣烫、四川火锅、香辣蟹,一波一波,一阵一阵,你方唱罢我登场,霸道地改变着上海人在浓油赤酱甜甜蜜蜜中培养起来的口味,谁说上海人不吃辣?去看看那些“辣馆子”门口排着的长队。
在二子哥哥家对辣的体验,当然也不止于那一次的饺子,还有火锅、跳水鱼、地道家常川菜还有老家带来的川味香肠。在之后的日子里二子家几乎成了我心中的,也使得四川在我心目中成为延安之后第二个让我希冀的地方。就连读《绝代双骄》时,见轩辕三光骂一句“格老子,龟儿子,仙人板板”我都觉得亲切无比。许多年之后,我第一次一个人走向成都,火车在秦岭的重重隧道中明灭,我啃着宝鸡站台上买的猪蹄,脑海中全是那些天府之国传说中的美食,浑身上下尽是即将梦想成真的快感。是夜,成都,我孑然一人徜徉在深夜的黑暗料理界,啃着人生第一个兔头,次日,我走进一家喧闹的小火锅店,在服务员尴尬的眼神下,点了一桌子食材,独自享用。人生美好,不过如此。上海的火锅店?不存在!
我没有办法将我在成都的欣喜若狂告诉当年的导师二子。那个小地方天南海北聚起来的人们,也在岁月这把杀猪刀的威胁下拖家带口各奔他乡。自从爸妈也回到上海后,那些老友也逐渐断了消息,终究成了过客,这其中就包括花子一家。我最后一次和二子哥哥的交集,还是录像带刚刚流行的时候,那个小地方也开出了录像带租赁店,寒假回到那里的我在二子哥哥的带领下,通过录像带这一媒介又打开了另一个花花世界。嗯,这厮总带坏我。
中国是红色的大陆,喜食辣之一味的远不止天府之国一方水土,我去到许多地方,那些有辣之故味的乡土总让我留恋。同理,辣味的体现也远不止辣椒一味,葱姜蒜乃至一些萝卜都会给人辣的体验。同样是一盘饺子,同样让我涕泪俱下,且痛并快乐着,却是一撮醋汁中的蒜泥,在山东费县的一家简陋的饺子馆。当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2018年3月11日于近水楼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