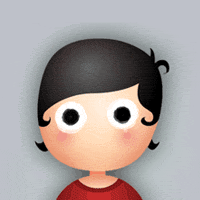祁媛:奔丧
我坐在火车上,回去为我的叔叔奔丧。叔叔死得非常突然,大约半个月前,我接到电话说他得了酒精肝硬化住进了医院。对于他得肝硬化这件事,我并不奇怪,我倒是有点奇怪他得的不是肝癌。叔叔是我见过酒瘾最深的酒鬼,他每天醒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喝酒。我印象里他几乎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整个人像是长期被酒精给浸泡着,醉醺醺的。一周前,叔叔的状况还是相对稳定,大家都以为他可以拖过农历新年,没想到昨天我就接到了他去世的消息。据说,两天前的早上,他还从病房里溜出去偷偷喝了一瓶白酒。就是这瓶白酒加速了他的死亡,他这样做无疑等同于。
不管怎样,叔叔的死是件很突然的事。我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想起半年前的一天中午,奇怪地接到叔叔的电话。爷爷死后,我们的联系就很少了,接到叔叔的电话,我本能地觉得出了什么事请。叔叔说要到杭州来,问他为什么,他也说不出,只支吾着说想来看看我。这让我纳闷,我从来没想过他会来看我,他从来就不喜欢我,他喝醉酒,倒是揍过我一顿,他掐着我的脖子使劲乱晃,差点没把我晃死。两个小时后,又接到他的电话,说是已经上了火车,但是火车上太热,他打算在下一站下车,然后回家,就不来看我了。不来就不来吧,这件事我也没放在心上。
现在,我要回去为叔叔奔丧了。我坐的是绿皮火车,这种火车没什么特点,就是慢和脏,就像某种人生。一对乞讨夫妻忽然大声唱着歌走过车厢,妻子用她烧伤了的手牵着她的盲人老公,并挨个向车上的乘客乞讨。她像一只母鸡一样带着她的盲人丈夫。已经是十一月了,她依然裸露着手臂上的大半肌肤,以展示她那烧伤过的像树皮一样纠结的皮肤,但是,丑陋和残疾已经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和同情了,他们在这节车厢里几乎没有什么收获,我想他们在其他车厢里也不会有什么收获。他们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给了他们一块钱,并不是因为我具有同情心,而是我觉得他们也算付出了劳动,应该得到报酬,虽然只是一块钱的报酬。
火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临时停车了,这里大概是个工业城市,我看到很多的烟囱矗立在楼房之间,在这样一个朦胧的雨天,城市安静得仿佛死了一样,只有这些烟囱静静地向天空冒着白烟。
四十二年前,一个美貌的中年妇女挺着一个五个月大的肚子去医院打胎。在此之前,她曾吃过两次打胎药,但是都没有把孩子流掉。肚子继续一天天地大起来,她一个人去了医院。她那个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医院拒绝为她做手术,说做手术对小孩大人都有危险,她又一个人慢慢地走回了家。五个月后,一个男孩出生了,这个男孩就是我叔叔了。
这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暴烈而又偏执的性格,他不爱上学,酷爱打架,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已经领着一帮小鬼每日在街上打架斗殴。叔叔很早便辍学了,整日在家无所事事,爱看武侠小说,喜欢射击,幻想过当军人。他去参军,没有成功,还学过理发,开过餐厅,但都失败了,他似乎做什么事都没有耐心,不能持久。可是漫长的时间该如何打发好呢,像大多数无聊的男人一样,他把时间花在了女人身上。这个无比懒散的男人却有一张异常英俊的脸,他好似从不缺女人。幼时的我经常在上学放学的途中看见他和不同的女人约会,但是其中只有一个女人让我留下了印象。该怎么形容这个女人呢,我是一个不会用形容词的人,只知道是她让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作漂亮。她也是叔叔的女朋友里我见面次数最多的一个,我一直以为他们会结婚的,可是他们最后还是分手了。分手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有一次天热,他们出去游玩,她穿着长袖的连衣裙,出了很多汗,叔叔闻见了她腋下的狐臭味,第二天便不再与她来往了。叔叔和她分手之后,她很受打击,之后的婚恋很不顺利。叔叔这边当然没有丝毫影响,他继续换着女朋友,没心没肺。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年幼的我竟然觉得叔叔离开了那个女人是件可惜的事情,他会后悔的。后来我还在街上遇到过这个女人,彼时,她已经四十多岁了,保养得很好,看上去依然年轻,生意也做得很好,是潭城有名的房地产商人。那时的叔叔已经变成一个为她工地每天拉石子的卡车司机。据说他们后面曾经相遇过,那个女人依然记得当年的事,耿耿不忘,她对叔叔说:“我会永远恨你。”
叔叔吊儿郎当混到了三十岁,女朋友找了一打,但是没有一个长久的,不是不联系了就是被叔叔打跑了。奶奶开始急了,托人给叔叔相亲。为了交差,叔叔去见过几个,不是嫌人太瘦就是嫌人太矮,总之是都不行。叔叔的工作也是一个问题。后来爷爷托关系,在单位里给叔叔谋了个临时工,一开始还好,时间一长,叔叔又干不下去了。他和单位的领导合不来,一天夜晚,他用砖头砸了领导的车,破口大骂,整个市政大院都可以听见他叫嚣的骂声。
没工作了,他又开始了百无聊赖的生活。没过多久,叔叔领回来一个女人,一个体态健壮皮肤粗黑的女人,长了一副肥厚的嘴唇,像两片黑香肠似的要把整张脸包住。有的时候我看她的脸,会有一种错觉,好像她那张脸上只长了一张嘴,其余的五官都可以忽略。我不明白叔叔为什么要和她好,因为在我看来,她不仅不好看,简直可以算难看了。我以为这次叔叔也会和以往一样,很快和这个女人分开,然后再换一个,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不仅没有分手,还很快结了婚,这个女人成了我的婶婶。
叔叔想结婚,爷爷奶奶自然不会反对,也许他们觉得一段稳定的婚姻可以让一个男人成熟起来。很明显,他们错了,叔叔是不会成熟的,他只会变老。婚后叔叔婶婶经常吵架打架,没有几天安生,一开始叔叔还占上风,但很快他就不是这个健壮黝黑的女人的对手了。这个女人习惯一边打一边骂:“你这只呆猪,傻子,窝囊废。”叔叔习惯了似的,听见就像没听见,这个从前的少女杀手,现在变成了他粗野妻子身边的一条狗。他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了一样,我感觉他身上的某些东西在一天天地死掉。他嗜酒的毛病也是从那时起,一天天地厉害起来了,他开始频繁喝醉,喝醉后就什么也不管地往床上一倒,口水就吐在自己枕边的床单上,他的房间总是有股闷闷的腥臊气味。婶婶大概也管过叔叔喝酒的事情,但是好像怎么都没有用,有时她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然后叔叔就去把她给找回来,再走,再找,再找,再走。他们俩好像都不爱对方,但是却又病态地纠缠在一起十几年。
他的妻子,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剽悍女人,有着母猪一般的旺盛生殖力。她为我叔叔总共怀过八次胎,流产流掉了七个,其中唯一生下来的是他们的第三胎即我的妹妹。我妹妹出生后,这个女人的性格更加暴躁了,她总是指使叔叔干这干那,干得不顺她的心,她就破口大骂。叔叔呢,也好像更履了,他成天为他的女儿洗尿布,为她的老婆洗内裤,干这些鸡毛蒜皮的烂事,完全沉溺在日常生活的琐碎和无聊中。他迅速地就衰老了,相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奇怪,原来年轻时长相好看的人有时比长相平庸的人老起来要更加的丑陋不堪,叔叔很快变成了一个庸俗甚至是有点猥琐的中年人。有一次喝酒,他醉倒在桌子底下,磕掉了半边门牙,从此叔叔好像更没有底气了,每次出门都站在他那黑胖妇人身后,心虚地微笑着。没有人瞧得起他,他的妻子,他的女儿,甚至是我也瞧不起他,爷爷对他似乎也不喜欢。只有奶奶,这个贫病的老妇人依然宠他,这个已然中年的男人有时喝醉酒还会扑倒在他母亲的怀里哭泣,背影远远看上去好像一只丧家之犬。
想到这里,我有点烦躁起来,突然想中途下车,折回杭州去了,就像叔叔那次来看我一样。不过这个想法也就是一念而已,车又开始缓缓地行驶。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街上的人也不多了,只有路边树上的彩灯还在不知疲倦地闪烁着,盲目地高兴着,也不知道在高兴什么。我已经想象到了我回家之后的场景:一个新寡的妇人带着她尚未成年的女儿,捧着遗像坐在地上哀号。无非如此,还能怎么样呢?可是当我走进家门的时候,这一幕却并没有发生。家里异常地平静安详,我婶婶在和她的母亲、妹妹躺在床上聊天,我妹妹正在玩电脑游戏。屋里的气氛出奇地温馨,我不由得怀疑叔叔是不是真的死了,直到我婶婶走出房间,看到她袖子上别着的孝带,我才再次确认这个家里确实有人去世了。婶婶的表情迟缓而平静,她对我说,你叔叔去世了,我们决定四天后火化,明天你陪我去医院给你叔叔打死亡证明。坟地我已选好,你可以去看看。你的叔叔留下两张银行卡,一张是他的工资卡,我已经领完。另外一张是你爷爷生前的银行卡,我不知道密码,你知道是多少吗?我回答她,是否为叔叔举办一个告别会,他的遗容可还安详,有否为他的遗体化妆?爷爷的密码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输爷爷的生日试试。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妹妹一直全程面无表情地参与着,既不激动也不伤心,趁我不注意,她把她的小拇指放进了鼻孔里面。你叔叔死的时候很安详,他不需要化妆,也不需要遗体告别会,没有什么人来。婶婶的回答把我从妹妹的鼻孔里拉了出来。
我们的谈话结束了,不到十分钟,但是已经把我叔叔的死亡和接下来四天要做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了。我收拾行李,原本以为要大哭一场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坐在凳子上开始有点无聊起来,也许是因为无聊,我开始感到饥饿,我想起来我还没有吃晚饭。
妹妹陪我一起去街对面的小巷子吃消夜,因为有消夜吃,妹妹似乎有些开心,但是她也许隐隐觉得这个时候为了吃而开心是不对的,所以极力克制住,勉强装出一副成人的懂事的伤心的表情来给我看,她知道我一直在看她。
走到原来熟悉的夜宵摊档,这家原来很火爆的小店不知为何生意变得十分冷清,店员们好似已经习惯了这种冷清,都在专注地看着电视连续剧。我的突然来到打断了他们这种闲散的状态,他们似乎有点不高兴。我点了炒米粉、烤鸡翅、花蛤和茄子,当我在冰柜挑选肉串和翅膀时,它们因为存放的时间太久吧,都已经冻住,并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我突然想起叔叔此刻也正躺在殡仪馆停尸间的冰柜里,他是不是也已经被冻住,像这鸡翅一样结起冰霜了呢,我忽然觉得他有些可怜。
因为店里没有生意,我们点的东西很快就送上来了,为了省时方便,原来烤制食物的炭火炉已经被电子炉所替代,全然没有了以前的味道。妹妹坐在我的对面,她胃口很好,一面对着电视机里的剧情哈哈大笑,一面大快朵颐,她好像是真的不伤心。妹妹十五岁了,肥胖而早熟,臃肿的身材就像她吃的鸡翅膀一样仿佛被注射过某种激素,被迅猛激烈地催肥了。她的体态神情早已不像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倒更像一个接近中年的妇女。我一直看着她,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的成长会这么畸形而快速。我依然记得妹妹八九岁时的模样,那时候的她已经有了少女的漂亮与妩媚,眼角仿佛好像经历过情事,连邻居家的老太太看见我都说:“你妹妹长得真像你,不过可比你漂亮。”妹妹的美仿佛具有一种野性,生猛粗野但具有活性,有着让人动心的力量。和她一比我简直就像一块木头。我看着妹妹,想起当年奶奶还在世时,有一次在饭桌上她看妹妹的眼神。我一看见那个眼神我就死心了,因为我知道奶奶永远不可能用这种眼神看我,那是一种打心眼里发出的爱与喜欢。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眼神,仿佛看一眼就得到了全世界的幸福。那时,妹妹还小,没有一点儿收入的奶奶用自己攒的私房钱给妹妹买了一个玩具大熊,两百块钱,这对奶奶已经是天价了。但是妹妹喜欢,奶奶没怎么犹豫就给她买了。这个玩具熊后来被妹妹暴力地把眼珠和鼻子扣掉,头扯烂,成为一块肮脏不堪的坐垫后,无情地扔进了垃圾桶。
妹妹在对面发出了愉悦的打嗝声,对于我这个姐姐,她基本满意,因为每次只要我回来,她都可以有几次这样胡乱吃喝的机会。听着她愉悦的嗝声,我打消了原本想要问她的问题:“你一点也不想你的爸爸,不为他伤心吗?”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不仅无聊而且幼稚,我为自己的幼稚哆嗦了一下,匆忙地付了钱。回家的路上,妹妹一路小跑,因为她知道我给她带了礼物,她迫不及待地要去拆开它们了。
家里客厅的中间摊着一条床单,大概是叔叔睡过的,上面堆着叔叔穿过的衣服、鞋子,还有为数不多的个人用品,也就是一两个茶杯,几瓶没吃完的药什么的。婶婶和她的家人在收拾,我问婶婶,叔叔的东西就这些了吗?全在这儿了?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稍微翻了一下叔叔的衣服,几件他常穿的衬衫和两件半新不旧的外套,一件棉袄一件大衣,两条西裤,几双旧鞋,这就是叔叔的全部东西了。我第一次发现叔叔的东西竟然比爷爷还要少,爷爷去世后,他在这个家里好像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不需要他这个不会挣钱的酒鬼了。婶婶倒是越活越年轻滋润了,家里到处都堆着她和妹妹新买的衣服、化妆品和皮鞋。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里面有一集讲母螳螂和公螳螂成婚交配后,母螳螂为了繁殖下一代,补充营养,就在交配后把公螳螂给活活吃掉了。
这夜,我一点也没睡好。屋外又传来了阵阵的猫叫声,是邻居家养的猫,到发情期了吗?不过这声音听上去更像婴儿在哭,微弱的,凄恻的,断断续续,一直到深夜还似有若无地挥之不去。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急促而又粗暴的手机铃声吵醒。我一看时间,六点钟,正打算继续睡过去,就看见一张肥厚的嘴,堵在了我的眼前。“你该起床了,我们今天要去医院,为你叔叔开死亡证明。”还没等我完全反应过来,婶婶那仿佛来自另一个维度的声音已经在我耳边响起。我渐渐清醒过来,想起昨晚婶婶和我说的话,是的,我今天要和她一早去医院为我叔叔开死亡证明,然后再去火葬场,再去看公墓,好尽快安排我叔叔的后事。
我们很快出了门,婶婶开着电动车带我穿过了闹市,几个月前还矗立在市中心的潭城一中已经变成废墟,我微微有些吃惊。城市到处都在翻新拆建,瞬间就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这种突然而又剧烈的变动让你分不清哪一种才是真实。街上的路人还不多,偶尔出现的几个人,脸上都是一副懒散而又麻木的表情,这是这个城市的人普遍的表情。太阳刚刚出来一个侧脸,环卫工人已经在打扫卫生,灰尘的颗粒在浮起的光线中若隐若现,我对着太阳看着颗粒在手指缝中穿过,内心突然有一种沧桑的微茫感。等红灯的时候,我看见分岔路的路面上有一只打散了的鸡蛋,一个小男孩拿着木棍在不停地敲打着鸡蛋,好像要把里面的蛋黄全部挑出来。蛋黄的半边躺在路面上,有点像今天早上的太阳。
街道并不拥挤,这个点就连每天在中心大街晃悠的疯子也都没有出门。没过多久,我们就到了医院,这家医院在今年全部翻新过,已经找不到从前的半点影子了。医院新盖的大楼外墙刚刚刷好漆,白得似乎都可以反光,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熟悉的了。我们上了十五楼,走过叔叔的病房,我停下来向里张望,叔叔的病床上早已经躺着一个新的病人。新的医院,新的病房,新的病床,新的病人,这些病人每天不停地在做生老病死这些毫无新意的事。
在婶婶等叔叔的主治医生的时候,我又在医院别处溜达了一下,偶尔路过一两处荒僻的走廊时,心中暗暗就想,这里会不会就是叔叔死之前喝那瓶酒的地方呢,他一个人在这儿喝酒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他知道这是他人生中最后的一瓶酒吗,他是在对酒这个老朋友告别还是在对人生告别?还没等我想完,给我们开死亡证明的医生来了,是个肥肥矮矮的中年人,脸色红润得几乎有点愚蠢。开死亡证明对他来说早已经是家常便饭。所以他办起这件事,轻松快速,他一边吃着早饭一边签完了字,表情甚至是愉快的。我猜他大概签字的时候一口咬到了他包子的肉馅,因为他的脸现在就像个肉包子一样。
我们下午去了公墓,这是一个荒凉的快被废弃的公墓,但是因为价格便宜,所以断断续续地还在维持着。穿着藏青色破旧大褂的看墓人领我们进了公墓,沿着长长的窄道进去,两旁的松树好似要拥抱我们,这样单纯的路我好像有好多年没有走过了,虽然这是个公墓,但是我倒并不讨厌这里,反而有点喜欢。在这条窄路的拐口处,有一大片圆形的墓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了。这些墓碑一层一层地排列着,墓碑与墓碑之间的距离不会超过二十厘米,每个墓碑所占的位置最多也就三十乘四十厘米那么大。在城市里的人,活着已经够拥挤,没想到死了却更加拥挤,这是否是人们不想死的原因之一?想到这儿,我不禁觉得有些可笑,看墓人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也许他觉得我在墓地里发笑是件很不严肃的事情。我懒得理他,继续看我面前的这些死人,看他们贴在墓碑上的黑白相片,看他们的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看他们有无子女,推算他们活了多少年纪,猜测他们的死因还有活着的生活又是怎样。这些人我没有一个认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瞬间,我好像都认识了他们,理解了他们。他们中很多人死的时候,比我年纪还要小,这么年轻就死了,是死于车祸,死于意外,死于疾病?我无从得知。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那么,我呢,我活得比其中有些人还要久,可是我又何曾觉得自己真正开始生活过。婶婶在和看墓人挑选墓地的位置,说是选其实就是随便乱指一块。婶婶这种挑选的姿态有点像扔垃圾,我说不出这样到底对不对,因为我也说不出挑选墓碑应该是什么姿态,也许从某方面来说,人死了埋在墓地里以后,就是一堆垃圾,一堆被上帝抛弃的垃圾。人的出生和死亡好像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人的一生又能够有多少自己的选择呢?不过也许选择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人生的道路,很多选择仿佛都是错的。
两天以后的清晨,叔叔的葬礼举行了,当音乐声响起的时候,他们都唱道:“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园在天上。”这齐声的合唱烘托出了一种人为编排的庄严感,好似一部通俗电影,非要制造一些情节,布置一下气氛,在故事的结尾烘托一下高潮,可是落入俗套,曲终人散之后回头再看,发现原来不过如此。想想也可以理解,因为大部分人的一生平淡无味,无聊漫长,于是不约而同地要在一些固定的情节上人为制造一些高潮,比如:出生,结婚,生子,死亡……他们自己是自己人生的导演,同时也是主演。可惜剧本大多抄袭,又缺乏独特性,于是就产生了无数的烂片。
妹妹穿着不知从哪儿借来的白大褂站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她知道她是今天的主角,所以一直在努力地扮演哀伤。可惜她的阅历她的智商不足以支撑她的演技,她很不入戏,总是四处张望,频繁地做小动作。不过,没关系,她的大部分观众也都不是想要认真看戏的好观众,就是来走个过场,无暇顾及她真的感受。蹩脚的舞台,蹩脚的演员,蹩脚的观众,还有妹妹身上不知从何处借来污渍斑斑蹩脚的白大褂,一切都是蹩脚的,就像叔叔的人生一样。除了请来的群众演员之外,真正来参加叔叔葬礼的人寥寥无几,也没有什么人真正的悲伤,这个潦倒、暴烈、愚蠢、失败的男人独自在人生舞台上演完最后一场戏,没有赢得一个观众、一点掌声,这世上除了把他生下来的母亲没有一个人真正爱过他。
到了火葬场,停尸间比我想象的要简陋,而且小得多,一排排不锈钢的冰柜年代已久,看得出被频繁使用的痕迹。叔叔的尸体存放在编号十七的冰柜里,被两个工作人员熟练地打开了。冰柜里是一个略嫌有些小的黑色廉价尸袋,鼓鼓囊囊的,拉链拉开后,我看见了一具双脚没有完全躺平弯曲着的尸体。可能是袋子小了的缘故,他脚上的黑色胶鞋也没有穿好,半套在脚上。由于生前疾病留下的腹水,他的肚子像孕妇一样肿胀着,脸则像冻过的绛紫色猪肝,嘴唇和眉毛都结上了薄薄的冰霜,五官依稀还可以辨认生前的模样,身上穿的白色丧服,做工简陋而粗糙,很明显是在小裁缝铺里低价定制的。我告诉自己,眼前这具浮肿而轻微扭曲的尸体就是我的叔叔了。谁能够想到这具即将要腐败火化的肉身也曾是个英俊的翩翩少年,他也曾年轻过,鲜活过,不过这一切都像淡淡的水彩颜料在洗漱池里被水彻底地冲刷到污秽的下水道里去了。
叔叔的尸体被抬上了焚尸炉的管道,甚至连尸袋也没有拿掉,脚也没有摆平,就被送进了焚尸炉,一切都是这么仓促,快到我都不及反应。此刻站在我身边的妹妹却突然夸张地放声大哭了起来,仿佛她把握好了节奏,就像是表演进行到最后一定要给你看的指定动作一样,她开始人戏了。我的婶婶,这个黝黑粗壮的女人,这时她轻轻地转过了身去,仿佛不忍看似的。我没有看到她是什么表情,但是她的背影告诉我,她还是有些伤心的,但是伤心的同时,她会不会也有一种解脱感呢?毕竟叔叔一死,她就可以彻底地开始她的新生活了,也许她一边伤心一边高兴着吧。
焚尸炉的窗口合上了,他们要像烧一块破布一样焚烧我的叔叔了。十年之内,我站在这个窗口外面,分别送走了我的父亲、我的奶奶、我的爷爷,然后是我的叔叔。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我们一家人同着一张桌子吃夜饭的情景,小小的方桌,每次吃饭的时候总好像很拥挤,奶奶负责盛饭,碗一只一只地传递着。夏天的傍晚,头顶昏黄的小灯泡被微风吹的左右轻轻摇晃,那时小小的我以为这就是一生一世了。十年过去了,他们都死了,我却还活着,我只是觉得疲倦。
焚烧尸体的师傅正悠闲地坐在一边抽烟,我忍不住向他要了一根,由于无聊,他主动和我攀谈了起来,并向我炫耀他的专业知识。他说道:“焚烧一个人的平均时间在一个小时左右,如果是老人或小孩还有干瘦的没有什么脂肪的农村人时间则更短,半小时到四十分钟就烧好了。中年、壮年、肥胖的都市人则要烧一个或者一个多小时,有肝病或者肺病的人烧的则要更久一些。”我默默地听着,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从他嘴里说出来,火化一个人就好似在做一道菜,都需要把握火候,不同的是做菜需要作料,而人却连作料也省了。我不由看了师傅一眼,他气色极佳,脸色红润,我情不自禁地想道,他的伙食一定很好吧。
我把烟头熄灭了,走出了焚烧间。妹妹和她的表弟在门口玩耍,有一种演出之后下场的轻松。我继续往前走,焚烧间的旁边是条土路,顺着土路走上去是一个小山坡,开采过的山,地表的岩石丑陋地暴露着,像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剥开了皮肤,露出了血淋淋恶心的皮下脂肪。坡顶聚集着密密麻麻的墓碑,还有一间简陋的小石板房,年迈的看墓人牵着一条狗在坡顶上站着,不知道为什么,这活着的看墓人比那些死者的墓碑,更让我觉得萧瑟和荒凉。山顶阳光很好,蓝天白云,却依然让我感觉这里是另一个世界,仿佛是活着的死后世界,一个和尘世无关的世界。我回头看见焚尸炉高高的烟囱里冒出的青烟,我的叔叔大概快要烧完了。十分钟之后,叔叔的骨灰从炉子里推了出来,因为尸体没有摆正,两根腿骨还是斜的。廉价的尸袋还没有被完全烧干净,有一些焦黑的化纤碎片,尸袋上的拉链也安静地躺在叔叔的头骨旁边,一看见叔叔的白骨,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自己夺眶而出了。
旁边一炉的家属走过来好奇地打量着叔叔的骨灰,探头探脑,神情悠闲的好像在菜场挑菜。这位仁兄十分钟之前还伏在他母亲的尸体上哀号不止,伤心欲绝,几近要哭死过去。师傅把叔叔的骨头从每个部位都截取了一块,放在操作台上碾碎,磨平,然后铲入骨灰盒,手法干净而又利落,像刀工很好的红案。在骨灰装入骨灰盒,盖上饰布,交到我妹妹手上的那一瞬间,妹妹原本平静的脸又开始准时悲号了起来。她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好演员。
我捧着叔叔的相片,妹妹捧着骨灰,我们俩走在最前面,其余的一行人跟在后面,我们一起坐上了开往叔叔墓地的大巴车。天空湛蓝,道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风吹过,还能闻到泥土和植物的气息。一年以前,也是这样的大巴车,这样的好天气,好得不应该办葬礼似的,所不同的是一年前的我回来是为爷爷奔丧,现在是为叔叔奔丧。那时我捧的是爷爷的照片,叔叔捧的是爷爷的骨灰,就坐在我的对面。谁都没有想到一年后的今天会是这样的场景。我在此刻似乎有点了解了叔叔,并且忽然无比地想念他。